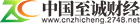《芭比》是一部好看的电影。它幽默、多彩、聪明,你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去解读它,每个人都可在其中看到「自己」,它创造了一个普世的话题,并对此保持开放性。
本质上,它是一部不加掩饰的写实作品。一顿花里胡哨的操作,是为了揭示生而为(女/男)人之苦。而对此电影跟我们一样,并无解药。
首先,整个故事的设置建立在某种倒错之中:芭比乐园就像是女儿国,在社会分工上芭比和肯们与现实社会中的男女是反过来的——这就是我们乏善可陈的想象力,对于弱者来说,还有什么是比翻身做主人更好的世界?上升的通道是如此狭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女性唯一的参照就是男性,因为所拥有的自由和权利是如此之少,她们不得不把自身困境投射到男性——更多自由和权利的拥有者身上。芭比乐园被从零开始推广父权制的肯们「颠覆」前后,经历了革命式的权力交替,政治斗争一般的策反和洗脑/反洗脑。这种如同讽刺漫画的叙述莫不照应了我们所身处其中的现实?女性只有模仿男性、把自己「变成」男性,通过某种异化才能得到些许自我麻痹的平等假象。
 【资料图】
【资料图】
我想到年初凯特·布兰切特主演的《塔尔》。在那部影片中,凯特饰演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指挥家。在开篇的一场对谈中,她针对主持人关于女性指挥家如何生存在这一极度男性化的行当的提问,给出了非常不以为意的回答,否认了自己身为女性的任何劣势,也不认为有任何性别不平等的存在。
我们看到一个男性化的女性,这里绝不是说外形,而是气质、用语、做派,她对男性的优劣照单全收,也允许自己犯一些很多男性都会犯的「错误」。
斗争者是否必须化身为其所斗争的对象才能胜利?换言之,是否必须通过成为你所抗争的事物的一部分是才算「上岸」?
而这些,往往是在现有条件下「弱者们」根本无暇企及的层面。格蕾塔诚实而巧妙地用一个金发碧眼大胸细腰的娃娃作掩护,讲出了这重困惑与矛盾。
让我们回看几部令格蕾塔崭露头角的过往作品。在她与伴侣诺亚·鲍姆巴赫联合编剧的两部独立电影《弗朗西斯·哈》《美国情人》(诺亚是两部作品的导演)中,她动情地描绘并演绎了这样一种年轻女性:她们踌躇满志,敏感而善于掩饰自己,有着恰如其分的才情却难以专注,屡屡碰壁,迷失在令其生存艰难又难以割舍的都市。
接着,在格蕾塔导演处女作《伯德小姐》中,一个从少女迈进青年的拧巴高中生在车上跟母亲激烈吵架,她说自己想要离开萨克拉门托老家,去一个「有文化」的地方,比如纽约。在《小妇人》里,乔为了作品得以出版答应给主人公一个结局——嫁人。
不难想象,女性与艺术,女性与创作,女性与金钱,这些是曾持续困扰格蕾塔自身的议题,也是她现阶段创作的核心。那些喃喃自语的话痨文青姑娘们,很容易唤醒你我身上苦心藏起的那个「神经病」,在被现实大口吞噬所谓抱负的最后一点模糊边界,发出微不足道的呼喊。
在影片最后,芭比乐园恢复「美好」,肯们也多了一点点存在感。而主角芭比却对自己的「结局」产生了巨大的困惑。换言之,被人类「感染」了的芭比有了思想——这种致命的病毒般的东西,其最大的伴生物就是痛苦。真实的人生更像没有奖励的打怪,没有「结局」一说。芭比创始人奶奶说:你想好了吗,要知道做人有时候是很不舒服的。
芭比做了一个只有人类才会做的决定,她迎着痛苦而去,不甘于作为某个被创造出来的形象,她想要成为创造者。这可以是动人的,也可以是徒劳的。
影片从死亡略过脑海的扫兴念头开始,到扁平足芭比踩着拖鞋看妇科结束,由始至终,格蕾塔投射了自己生而为人,尤其是生而为女人,进而生而为一个以创意活动为生的女人,在白人主导的西方父权制社会中的生存体验以及对自身存在性的思考。
格蕾塔以辛辣但不怀恶意的方式嘲讽并自嘲的,就是世间男女不得不日日逼视的「我」之深渊:巨婴症,坐以待毙却祈求天降「达西先生」;脆弱的自尊与迎合权力的媚态。现实中,它们远没有电影里那么好玩。
而它们多半为了消解这样一种沮丧的事实,到头来,抗争不能说是完全没用,只是……几乎没用。假以时日,肯们获得的权利也许会跟现实世界中女性获得的一样多;你终于舍得脱下那身不合时宜的皮草,却依然渴望一条法官的袍子来确认自己是谁。
多么「令人鼓舞」,但这确实是微弱的进步。
这样一部由女性创作者主导的《芭比》的出现就是其现实的映照。它以主动的姿态真诚地描摹了人的处境,不论男女,性别都不只是生物学,它是我们主动加在对方和自己身上的枷锁和借口,而我们一次次深陷其中,搞不清状况。芭比的前世在芭比乐园,今生恐怕就是弗兰西斯·哈或伯德小姐,她会以为自己有才华,她会奔跑、摔倒、失意、宿醉。她会把错误一一犯个遍,感到迷惘和疲惫。
整部影片中格蕾塔只给观众留下了一句话作为「希望」,不是那段长篇大论的檄文,而是Z世代小女孩萨沙劝妈妈回去帮忙拯救芭比乐园时说的,就算不能彻底改变什么,至少可以让情况好一点点。
我们不就是以这样一句「废话」为信念日复一日地推着石头上山吗?
格蕾塔带来了一种清新的女性叙事。它不是史诗级的老辣,那是不可能的。这种叙事带着清新、稚嫩、矛盾,就像书写它的作者和无数将在其中看到自己的女性一样。它也像《美国情人》结尾里女主屡被拒绝最后自立门户成立的文学社,你可以说它是过家家式的自娱自乐,但它真的有一种笨拙而迷人的独特气息。
而当想到共同书写这样故事的,还有一位资深的男性独立导演,也觉得更鼓舞人心那么一点。
下一篇:最后一页
-
《芭比》讲出了格蕾塔的困惑与矛盾
2023-08-01 -
北新路桥拟定增募资不超17亿元 控股股东参与认购
2023-08-01 -
美佛州州长称特朗普无法在大选中获胜:“这都是事实”
2023-08-01 -
海评面:大运村的生日礼物让人“开心到飞起”
2023-08-01 -
金阳新能源(01121.HK):就硅片项目订立租赁协议以租赁徐州大黄山街道物业
2023-08-01 -
科普|肿瘤标志物:名字使人慌,作用却很强
2023-08-01 -
小米旗下的有啥手机
2023-08-01 -
为花草树木“解渴”
2023-08-01 -
美国航天局尝试联系“旅行者2号”
2023-08-01 -
豪江智能:外销收入占比较高
2023-08-01
-
8月1日金象珠宝黄金583元/克 相比昨日上涨3元/克
2023-08-01 -
牛杂和小青菜怎么烧好吃?
2023-08-01 -
奥华简装变豪装丨周年庆典礼遇万家!第一阶段完成率151%销售额突破180万
2023-08-01 -
57天完成一次出舱任务 神州十五号航天员今见面
2023-08-01 -
广东正推动放宽广州、深圳“限牌”支持广州、深圳等汽车大市实施购车补贴、以旧换新
2023-08-01 -
海外网评:21世纪了还在压榨童工,美国病得不轻
2023-08-01 -
8月,日本五大银行上调房贷利率
2023-08-01 -
那时候的天空很蓝是什么歌(那时候的天空是蓝色的出自什么歌)
2023-08-01 -
【环球财经】澳大利亚央行再次保持基准利率不变
2023-08-01 -
万凯新材:7月31日融资买入280.75万元,融资融券余额1.4亿元
2023-08-01